某校《高分子物理》课期末考试的“英文名词解释”题中,考到“rotational isomeric state”(旋转异构态)这个术语。我感到很困惑。因为这个术语是比较深的。我们所采用的本科高分子物理教材,根本没有涉及到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甚至没有出现在P. J. Flory的“那本书”——Principles of Polymer Chemistry中(出版于1953年),因为这个概念是由Михаи́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олькенште́йн(M. V. Volkenstein)在1959年发表的著作Конфигурационная статистика полимерных цепей(聚合物链的构象统计)中正式提出的。1963年,该书的英文翻译在美国出版,P. J. Flory在序中高度赞赏了该著作。后者的“另一本书”——Statistical Mechanics of Chain Molecules也于1969年出版,使得旋转异构态——计算真实聚合物链统计性质的一种近似思想——得到更加为人所知(尽管这本书仍然是少有人阅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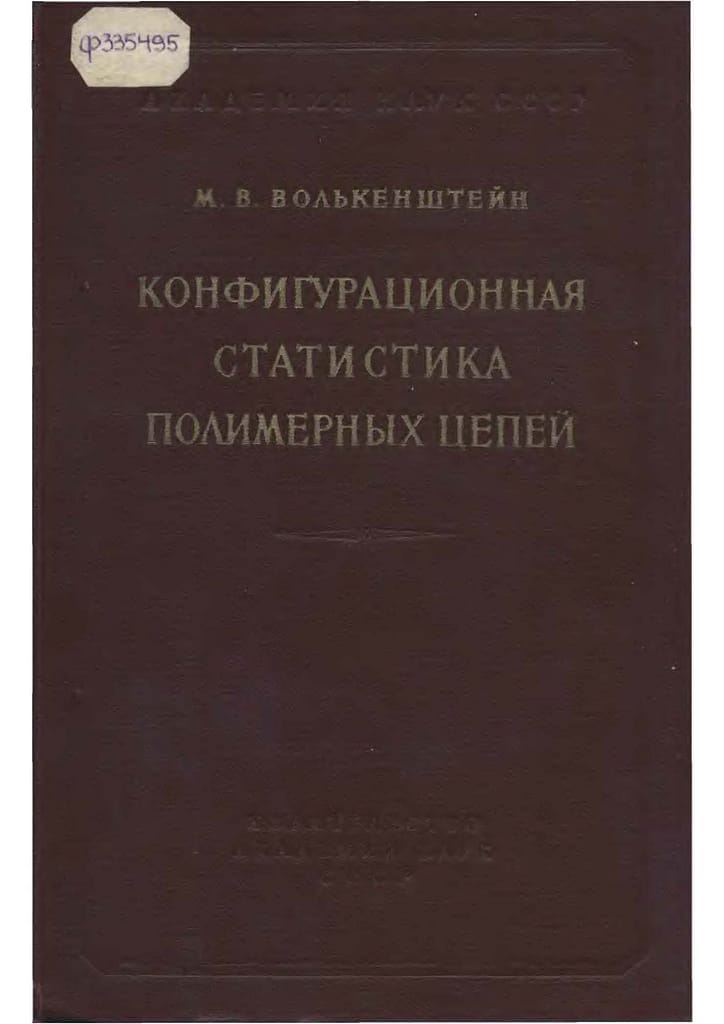
旋转异构态假设,使得描述真实链的化学键节复杂性——例如不对称以及各自不独立的键节旋转势能曲线——有了可写下的统一数学形式。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一假设造成的好处是数学描述的离散化。这很像由“随机过程”到“时间序列”的变化方式。
上世纪60年代恰好是电子计算机问世的时代。复杂的计算如果可以被以一种离散化的方式描述,就可以通过电子计算机来解决。基于矩阵运算的线性代数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以马尔可夫过程为模型的预测,其实是落实到转移矩阵的运算上。同理,基于旋转异构态假设对真实链进行离散化描述后,有望通过计算机,给定化学式,预测出链统计结果——这将进一步用于预测聚合物材料的许多性质。这无疑是令人兴奋的。但是作为一门科学,这一假设是否符合实际,需要实验验证。而实验的可验证性理论,是任何一项理论工作的“另外50%努力”。Volkenstein原书总结了大量可能用于验证这一理论的实验方法——包括偶极矩测量、光散射、Kerr效应等。但是这些实验方法与旋转异构态假设正确性的联系,依然藏在复杂而间接的数量关系以及更多实验假定(比如valence-optical scheme)之下。
从今天的角度看,高分子物理理论的发展与液体物理的发展若不能说是同时的,则前者甚至超前于后者。因此,成功的高分子物理学家,免不了要在液体物理问题上有先锋式的正确认识。这在Flory的Principles in Polymer Chemistry一书中是有所体现的。例如在溶液热力学的格子统计部分,Flory“啰嗦”了一段话(p. 497 sec. 1a的第2自然段),实际上道出了液体的径向分布函数概念!反之,Volkenstein的原书,反映了前苏联科学家在Валенти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Каргин(V. A. Kargin)关于液态的落后认识的影响。在Kargin当领导的期间,这些观点是用来对抗来自美国同行的不同观点的。Илья́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и́фшиц(I. M. Lifshitz)的更加正确的高分子物理观点(1968年)被推迟到斯大林时代之后才为人所知[1]。因此,今天再想了解这部分内容,应该直接看Flory的著作。Flory的著作包括了他本人和后期的几个同事和学生:J. Mark、A. Abe、R. Jernigan、A. Tonelli的后续工作;他们发表了同一物理量的理论计算和实验测量结果比较,十分完美的印证了Volkenstein链统计理论的成功,比如以下著名插图。

References
- A.Y. Grosberg, and A.R. Khokhlov, "After-Action of the Ideas of I.M. Lifshitz in Polymer and Biopolymer Physics", Advances in Polymer Science, pp. 189-210, . http://dx.doi.org/10.1007/12_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