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准备关于布朗运动的课程讲义,翻了很多随机过程的教材。我关注的重点仍是用少之又少的学时传达建模布朗运动所需的随机过程知识(或仅仅是思想),所以筛选的是一些简明教材。当然我自己为了扎实也看了很多形式严格的书,包括王梓坤的书。
让我特别想写下这篇博文的是一本湖南大学出版社的《随机过程》,作者是湖南大学的吴俊杰、合肥工业大学的潘麟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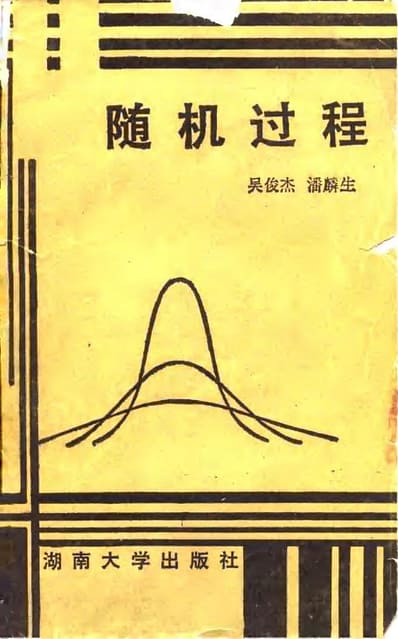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好,它做到了以最少的篇幅,提供最必要的知识。作为应用数学教材的作者,它很难预知读者都是什么领域的。这需要凭教学经验知道,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一般缺什么知识。在严谨性上,在意什么方面,不在意哪些方面。更重要的,作者需要自己有一个很profound的understanding,在关于:“哪些内容是必要的?为什么?”——这个问题上有明确的观点,一方面主导着他为少学时课程和初学者节选内容,另一方面使他能把所节选的内容讲得十分coherent。也就是说,这个作者自己需要已经“把书读薄了”,而且是把书读成几种版本、面向不同读者的“薄”。从这些角度去评判一本教材的内容,很容易鉴别一本简化了的所谓“少学时”教材是否是一本四不像垃圾,以及这个教材的作者“是不是真的懂”。
我发现吴俊杰和潘麟生的《随机过程》经受住了所有这些考验,因而应是一本经典。只可惜它埋没在了大量同名教材当中,在“中文教材滥觞”的灾难下形同消失。就算偶然被人从图书馆翻到了,也由于它极其modest的封面、印刷和那“毫无特色”的前言,被评一句“毫无特色”。所幸,两位默默无名的作者曾在《大学数学》上发过一个小豆腐块儿,谈了一下编这个教材的想法和过程,我十分建议大家去读它,我就不在这里全文复制粘贴了。
我认为“教材的书评”这件事情(属于评价学层面的讨论了)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在教学实践当中经常面临的就是学生基础背景跟学习目标都跟你实际了解的知识差距非常远。你完整懂了一个全集,却并非一劳永逸,而是每每要根据不同的学生群体重写“阉割版”讲义。评价一门课或一个讲义,永远是对简化之后的产物进行评价。任何一个标题(例如“随机过程”、“多元函数微积分”等),明明正确知识只有一个版本,却出现这么多教材,能作为评价原则的也就是评价它们:1) 为何简化;2) 如何简化;3) 利与弊,目的达成与否。国外教材,作者一般会在Preface或Introduction中自己阐述这些问题。国内教材(指用心写了的少数),无非吃亏吃在了中文文化中“少展露个性思想”的惯性。
像这两位这样的教科书作者,也许不多,也许不少。其实学术著作,就算是大学本科的教科书,也是常常首次出版之后,只印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重印了。因为同类教材多如牛毛。自己在有限的教学生涯过程当中总结了一个讲义,出版成教材后,最多也无非是本校本院会去采用(有时甚至未必)。不作特别宣传的话,全国难有其他高校去采用。教材的口碑市场,本来就比学术论文的更薄弱,而且在我国尤其如此。我想像在那个还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也许与教学相关的国内会议中,各高校教研组的老师能有一些交流,一些教研方面的期刊会有一些书评,也就最多如此了。出版社除了那些列入“十X五”、“新世纪”等“工程”的教材项目之外,是否再印一个“普通地位”的教材也完全看市场。图书馆的架子,成了大多数真正脱胎于教学过程的教材的生命终点。
我总认为国外的情况稍好一些。在上世纪互联网时代之前,学术传统就已经很发达,大量师承关系从19世纪开始就没有断过了,教材的口碑市场至少仅靠口口相传的基础都非常强健。这也可以从很多出版社不仅重印经典,还以冠以“经典系列”作成丛书来重新出版(例如Dover Publications就做过很多这种事)。反观,我国只有80年代之后才算开始从零形成正常的学术环境,学术师承就几乎免谈,再加上高等教育的苏式和计划特色,教材市场在完全没有口碑机制的社会要么依附权力、要么野蛮生长。国外在有了amazon.com之后,更是更多原本无名教材复活的春天。Amazon.com是教材书评方面的佼佼者。我认为amazon.com的存在使得英文教材的口碑市场进入了新的时代。我从我所看过的教材以及amazon.com上的评价看到的是:国外的教授会上网,amazon.com有他们上课使用某教材时的评价;国外的研究和开发者会上网,amazon.com有他们做项目时要恶补某知识时使用某教材的评价;国外的大学更是会上网了,amazon.com有他们要辅助课程学习、找练习题、过期末考时,对某教材的评价;last but not least,教科书作者本人也上网,很多畅销教科书的再版又再版,就是参考了amazon.com上的评价进行改善和更新的——一种非常市场化的教材撰写模式。这在我国仍然是也将继续会是空白。首先我国的互联网是被有意地限制其社会功能范围的,这也导致了其次,除了学生之外学术界的其他角色根本不上网。国外像上述那般因amazon.com而进入了新时代的事情,在我国是不会有的。
我国本来就没有享受到西方那样的连续的现代史和科学史。半正常地发展了短短几十年,世界又深化到后现代了,包括“科学”在内的原本光荣神圣的“现代性代表”已经过时了。中国到底能赶上哪一拨呢?
Parzen的书特别引用过同时代的宇宙学研究(p.71)。就是把当前这一个宇宙看作一个随机过程的某次实现。想从这一个实现来研究统治这个宇宙背后的分布函数。所以,这个宇宙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一次随机实现而已。中国赶不赶得上哪一拨,who ca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