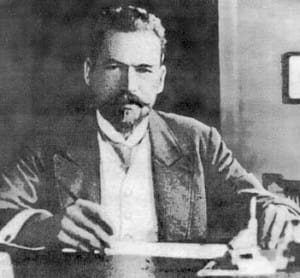有几首Disney的歌曲总是能让我有想哭的感觉。我总结了一下原因,发现这些歌曲都很像妈妈哄孩子睡觉时唱的那种歌。
欧美流行曲
我听Disney歌曲是上初一的时候。上初一之前我几乎不知道英文流行歌曲,上了初一之后不知道为啥就流行起来了。至少是买了Walkman,在学校可以听卡带。家里也有音响可以播放CD。那时候有Now系列的欧美流行曲集锦CD,我买过的就有Now One和Now 3。除了集锦碟之外,还迷男声组合,除了Backstreet Boys之外,还有Boy Zone、Michael Learns to Rock之类的。有一个比较不那么有名叫Code Red的当时也很迷。网上还真能找到当年他们最红的主打歌呢(下面的视频图像和歌不是对应的):
不过很快我的兴趣就不在这类歌上面了。当时刚好《狮子王》卡带出来了,于是我日日夜夜听的就是《狮子王》音乐。有了Walkman不久我就去找哪有卖卡带的。很容易找到那种“奥斯卡电影金曲”、“葛莱美金曲”之类的卡带,因此也听了很多电影主题曲。我印象最深的(我听过的最好听的)主题曲是Evergreen,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哪部电影,但是它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非常美。我渐渐发现,我听歌还是比较在意歌词本身美不美的。不过这首歌没有典型的Chorus部分,歌词从头到尾没有重复的,很难记忆。
[audio:https://www.andrewsun.net/panta_rhei/wp-content/uploads/2011/03/7f35e4172200fe390a589e5ab79b521b.mp3|titles=Evergreen]
Love soft as an easy chair
Love fresh as the morning air
One love that is shared by two
I have found with youLike a rose under the april snow
I was always certain love would grow
Love ageless and evergreen
Seldom seen by twoYou and I will make each night a first
Every day a beginning
Spirits rise and their dance is unrehearsed
They warm and excite us, cause we have the brightest loveTwo lives that shine as one
Morning glory and midnight sun
Time weve learned to sail above
Time won’t change the meaning of one love
Ageless and ever evergreen
那时我如此喜欢这首歌以至我不厌其烦地倒带重听,后来我都能够很准确地倒到开头了。
Disney歌曲
一直以来Disney音乐我就是听那盒《狮子王》,直到有一天我经常光顾的卡带店里卖了两个封面有个大米老鼠头的录音带,一个是红底的,一个是蓝底的。那就是Classical Disney的第一和第二辑。现在这套系列一共有五集,但我很长时间都以为只有两集。我当时虽然家里给我买的东西不赖,但给我用的零花钱是很少的。录音带要自己买,我还不够钱一下子买两盒,先买了一盒,听了半个学期,就又再买另一盒。从此我一直以为我买齐了整个Classical Disney。
那个时候,除了中国播放的米老鼠和唐老鸭系列之外,我没有看过一部迪士尼电影,包括《狮子王》。因此,这些迪士尼电影我都是从它们的歌曲先接触的。有些歌曲实在太美妙,让我简直在脑中就已经浮现出动画的场景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小美人鱼》的音乐。像Under the Sea这么缤纷热闹让我想到MTV是在夏威夷取景;Part of the World的歌唱者透着情绪的语气让我似乎直接看到了她脸上的表情,美妙的嗓音也让我把主角的样貌想象得特别美丽;最让我着迷的还是Kiss the Girl,那是深蓝色的、树影婆娑的夜里,啾啾的声音其实是来自海洋的精灵们悄悄制造的音乐,随着歌曲的继续、精灵们神通渐显,夜色越来越多彩迷人,最后,王子到底亲吻了美人鱼没有?乐曲没有交待。
[audio:https://www.andrewsun.net/panta_rhei/wp-content/uploads/2011/03/Kiss-The-Girl-The-Little-Mermaid-1989.mp3|titles=Kiss The Girl (The Little Mermaid 1989)]
歌词本身不赖,但主要是唱得非常好。另外一首Poor Unfortunate Soal,堪称绝唱!这首歌的歌词不错,还“body language”呢……我认为这是全剧最棒的歌。顺便提到我认为《狮子王》最棒的歌是Be Prepared,也是一首坏人唱的歌,有趣。
[audio:https://www.andrewsun.net/panta_rhei/wp-content/uploads/2011/03/Poor-Unfortunate-Souls-The-Little-Mermaid-1989.mp3|titles=Poor Unfortunate Souls (The Little Mermaid 1989)]
多年之后我有机会找到《小美人鱼》的电影来看。本来认为自己完全凭空在脑中想象的场景一定是比实际要美好得多,准备失望的。让我意外的是实际电影的场景丝毫没有低于我原有的想象,有过之而无不及。确实感到Disney的伟大,它能够表现出极尽人之想象的画面。真让人心疼得想哭啊:
还有一些年代更加久远的歌曲,来自的电影名称我听都没听说过的,但是歌曲却让我感动得落泪。其中一首叫Candle on the Water。动听的钢琴音带进温柔的妈妈唱歌哄我睡觉,歌词充满了真善美。
[audio:https://www.andrewsun.net/panta_rhei/wp-content/uploads/2011/03/Al-Kasha-and-Joel-Hirschhorn-Candle-on-the-water.mp3|titles=Al Kasha and Joel Hirschhorn – Candle on the water]
我上Wikipedia.org找了这首歌的介绍,影片中这首歌出现的情节是非常感人的:
The setting for the song is entirely on the lantern room balcony of the lighthouse in which Nora and her father Lampey live. Nora sings the song to her lover Paul, who has been lost at sea for over a year but Nora believes will one day return. Her father one evening mocks her about this, and she retires to the lighthouse balcony to sing toward the ocean, assuring Paul that she is still waiting for him.
不过,这也道明了歌不是妈妈唱给孩子睡觉的。另一首也让我落泪的歌,经了解后,确实是哄孩子睡觉的歌,那就是Feed the Bird。这首歌的歌词美得那叫一个心疼!
[audio:https://www.andrewsun.net/panta_rhei/wp-content/uploads/2011/03/Richard-M.-Sherman-and-Robert-B.-Sherman-Feed-the-birds.mp3|titles=Richard M. Sherman and Robert B. Sherman – Feed the birds]
Early each day to the steps of Saint Paul’s
The little old bird woman comes.
In her own special way to the people she calls,
“Come, buy my bags full of crumbs.Come feed the little birds, show them you care
And you’ll be glad if you do.
Their young ones are hungry,
Their nests are so bare;
All it takes is tuppence from you.”Feed the birds, tuppence a bag,
Tuppence, tuppence, tuppence a bag.
“Feed the birds,” that’s what she cries,
While overhead, her birds fill the skies.All around the cathedral the saints and apostles
Look down as she sells her wares.
Although you can’t see it, you know they are smiling
Each time someone shows that he cares.Though her words are simple and few,
Listen, listen, she’s calling to you:
“Feed the birds, tuppence a bag,
Tuppence, tuppence, tuppence a bag.”
歌词为什么好?用中学语文课的理论来讲,就是“有点有面”、“有人有景”。既有特写老人家的部分,又有描写大场面的部分。而且大场面那一段的音乐转折非常动人,是个大调转小调。
从歌词来看,到While overhead, her birds fill the skies这里画面就要扩大了。我们的视角就似乎跟着这些birds上升到了天空,向下俯看,整个大教堂尽收入目,廋弱的老人家的身影想必显得十分渺小。这时音乐还是大调。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教堂壁画里的圣人先知在看着老人:All around the cathedral……歌曲伴奏乐团的管、弦声部都一起用了,还转小调,真是沁人心腑。
除此之外,全曲最让人纠心的是“Their young ones are hungry; their nests are so bare”这句。歌词的立意非常真善美。记得这首歌是在第二卷的卡带B面的第一首,因此很方便我重听。初中那会儿,多少个晚上我睡在宿舍床上,就是一遍一遍地倒带重听这首歌而入睡,有时真的能听得眼角渗泪。回想起来,虽然现在我成了一个又丑又贱的烂人,但我小时候还真是个心灵柔软的小正太哎!
这首歌出自1964年迪士尼电影Mary Poppins。中文叫《欢乐满人间》。在电影中这首歌就是Mary Poppins唱给两个孩子,作为摇篮曲的。多么温柔,多么循循善诱啊。它教育孩子同情弱者,充满了真善美的力量!全曲除了有教堂的场景之外没有任何宗教说教,但我却不得不希望世界上有天堂,以便这位孤苦仱仃的老人的结局能让人满意。
现实并非那样美好。圣保罗大教堂并非冷寂空旷,相反作为旅游名胜这里往往是人气鼎沸。因此实际上为了卫生的缘故,管理者打出了“请勿喂鸟”的告示。我想,多少看着Mary Poppins长大,专程到大教堂“感怀”一番的游客看到这服告示会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