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切入大幅振荡剪切流变学这一领域的时候,从1835年Webber的那篇讲蚕丝蠕变的文章起,一共收集了近500篇paper(包括1841年柯西在数学上描述材料形变的记忆效应的文章)。我主要收集的是聚合物的非线性流变学理论和实验的文献,尤其是振荡形变法。虽然这么多篇文章的内容我不一定都记得,但是一些经常出现的人名,还有一些虽然出现得少但被公认为大牛或元老的人,我还是知道的。今天我把本博客主页右边的“流变学家”栏目完善了,根据的就是我从看paper过程中了解到的一些牛人,有死了的有没死的。其链接都是找的最有代表性的网页或文件。其中有一个人让我找得最辛苦,那就是W. Philippoff。这个人你在Google上除了他写的文章之外基本上搜不到任何相关信息,没人给他颁奖、写讣告或者纪念作传。
但是,W. Philippoff绝对是牛人。能在Weissenberg八十岁诞辰纪念集中写文章的都是流变学的牛人,而且我也有好几篇Philippoff的文章。我记得这个名字,最初是觉得这个词很可爱。经过努力,终于搜到R. Tanner曾经在Korea-Austr. Rheol. J.上介绍过这一段历史,可作为对Philippoff致敬的代表性文件添加到W. Philippoff的链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左边点击W. Philippoff的链接看看这篇文章。原来,是W. Philippoff全名是Wladimir Philippoff,用全名去Google倒还能找到他获颁Bingham奖的信息。我一直还以为最初用正弦振荡形变的是Weissenberg呢。不过也差不多,因为Weissenber在那时是Philippoff的同事。
之所以会想到用正弦形变,其实是有背景的,1850年左右,开始有电话。由于音频是快速变化的电流,距离一长了的话介电损耗的影响就很可观,于是采用正弦交变电压研究材料的介电损耗就慢慢兴起了,损耗角正切tanδ之类的概念也是从那里来的。这种知识到了1933年Philippoff发明正弦形变的时候已经是电气工程的基本知识了,而Philippoff恰恰是学电的,所以他想到把这一套东西运用到流变学上面去。照这样的说法,那么五,六十年代的文章中出现用Lissajous曲线表征材料非线性响应的做法,就更加不算什么创举了——Lissajous曲线就是交流电方面的基本知识。到现在,我们还在用动态扫频实验来探测许许多多的材料结构,几条Lissajous曲线还足以让McKinley他们在Soft Matter上发文章,足见Philippoff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多么大的饭碗!给后人提供很多饭碗的人,其实就是诺贝尔奖级别的人(那些诺奖得主无非不就是为后面的平庸同行创造了个持久耐用的饭碗么)。
所以Philippoff是牛人是绝对不差的。
我还无意中找到了Philippoff的亲笔签名!那是在G. Natta的纪念网站上找到的。G. Natta就是齐格勒-纳塔的那个纳塔。在他网站收了他的书信,并按去信的单位分了类,其中一个就是Esso Research & Engineering(就是埃索汽油吧),而Philippoff就正是Esso的人。书信集里收集了也许是所有Esso人员与Natta的书信来往,多数是与Natta联系学术访问的,看看那时候的人互相学术访问搞讲座的潮流也不失种趣味。其次就是向Natta索要等规聚丙烯样品来玩的。等规聚丙烯恰恰就是Z-N催化剂的举世成果,在那个时候也许只有Natta的实验室才能做得出来。有趣的是,Natta也求过Esso研究所帮他测等规聚丙烯的分子量,结果Esso研究所回信说没有仪器,测不了。哈哈,跟现在比起来,那个时候真菜啊!
所以,在书信集里我就找到了Philippoff的信,只有一封,是联系访问Natta的实验室。Philippoff的回信末尾,就附了一个亲笔签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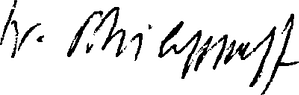
Update 2021:原文所说的“G. Natta的纪念网站”,现在找不到了。这个网站是更加全面的G. Natta生前资料存档网站,但也很难找出原文所说的那些信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