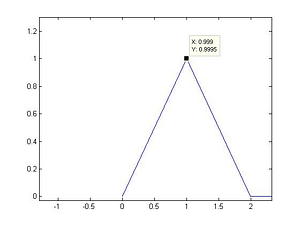前面发表了头四天的交流总结。第五天(周五)我照常去实验室,但是没有太多的正式交流。由于德国纬度高,这个季节天黑得很晚,所以我周五离开实验室之后仍然有几小时游玩的时间,加上周六一整天,我得以在Karlsruhe城逛了一圈。不过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写含有个人感想的游记。只能先把我回国后逃不掉的功课先做了。有很多内容其实都是从Wikipedia.org等地方弄过来的。
 |
| 05-15-2011 Karlsruhe places |
Karlsruhe的概要
完整的概要直接去Wikipedia.org看就行了。我总是特别不复述一些早就有的知识,哪怕我自己是刚学到。我刚学到是一回事,复述出来就很丢脸——哦,你才知道啊?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知道了!所以凡是我认为一定早就很多人知道,或者在图书馆肯定有书记载的事情,我就都默默学习完了就拉倒,而不会兴高采烈地复述和抒发“原来XX是XX的哦!”这种十分丢脸的事情。我既然认为这样丢脸,那就是说明我会鄙视这样的人。经常把“原来XX是XX的哦!”这种句式挂在嘴边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很后知后觉,慢半拍,不想理他。每当我看到别人对我已知道了一百年的事情作出恍然大悟的表情的时候,我心里就要尽力提醒自己不要产生卑鄙的窃喜和嘲笑,但往往仍然按捺不住眼角的冷光……人是应该以没有在一生出来就知道全人类知识为耻的。未来的一天人的科技应该发展到使得人一生下来就已经获得已知的知识,而把宝贵的整个生命放在获得新知识上面(当然还是要花时间培训获得新知识的方法)。
当然,如果这都要“以为耻”那岂不是每个人都要羞耻地活一辈子?这恰恰就是“严格要求自己”的表现。很多人是在另一个极端活,就是非常放松自己。放松自己不是不可以,但是要“以为耻”。例如我就经常放松自己,打帝国时代。但是我以为耻啊,所以就可以。有的人也打游戏但居然“以为荣”,那就不行。所以根本并不在于你做还是不做,而是在于荣耻观。很多人觉得“反正都要放松自己了,有荣不去以为何苦非要以为耻呢?”那不行。荣耻观很重要。
所以我写博客是游记不是游记、日记不是日记。基本上标题是骗人的。这使得我自己想找回以前一些特定内容都往往十分困难。为了方便自己还是要写回一些扣题的内容。
Karlsruhe又名风扇城(fan city)就是因为它的道路设计是以Schloss为中心的同心圆形式向外辐射的。这是建城的时候就这么设计的。看地图内容这么丰富以为城市不小,结果我从北边的Schloss走到南边的Hauptbahnhof还不用十五分钟。要知道我每天从家里走到实验室都要半小时了……
Karlsruhe城二战的时候被盟军炸过,后来有所恢复。所以难怪Marktplatz那里的教堂和city hall都好像完全翻新过一样,尽管风格是“修旧如旧”。虽然Karlsruhe很小,但是关于Stadtwiki Karlsruhe网站却是现在最完善的关于城市的wiki。现在那些广州仔不是说要“撑粤语”么。他们这么“潮”,什么时候弄个广州市的wiki就够“撑”了,而且也显得有点文化,不光光只是去江南西静坐之类的。
现在的KIT是2009年由Universität Karlsruhe-TH和Forschungszentrum Karlsruhe合并而成的。 后者在战后是西德的核武器研究所。冷战结束之后,失去了原先的角色,空有研究实力但没学生。而前者有学生,于是两者就合并。Forschungszentrum是现在的北校区,Universität是现在的南校区。我去交流的institute是原来的Universität下面的,所以在南校区(上图)。
KIT没有围墙,在城里走着走着就进大学了。但有个老校门在Kraiserstrasse。校门写着Technische Hochschule,这是Universität Karlsruhe老名字,也是为什么Universität Karlsruhe后面总是附个(TH)。就好像华南理工大学以前叫华南工学院一样。
Schloss
Schloss是Karlsruhe城市的标志性地点。它是一个宫廷。在它后面(北面)有一个后花园。我到的时候是早上八九点,基本上没有人,耳边只有大自然的声音,感觉非常舒服。我在中国很难找到这种感觉,到处都是人,把自然挤没了。所以我又要老调重谈了,西方文明重天理轻人伦,中国文明重人伦轻天理的原因就在于此。成天看到的都是天地,看不到一个人,你是很难去想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只能想到人的渺小。人一感到渺其实就是产生了宗教体验。
我录制了一段展现后花园景色的有声影片:
Marktplatz
Marktplatz是Karlsruhe的闹市区,北边打横的Kraiserstrasse就相当于广州的北京路差不多。在Marktplatz有Karlsruhe的又一个城市标志——金字塔。它是纪念传说中的城市的建造者Margrave Charles III William。在金字塔两旁是Evangelische Stadtkirche(教堂)和Rathaus(市政厅)。再往南是Charles Frederick的铜象,他是巴登的ruler之一,年代大至上是跟莫扎特差不多,恰好是这个Charles在任内废除了农奴制。废除农奴制是那个时代的主题之一。
Karlsruhe的教堂
我特别踩了Karlsruhe城里的好几个教堂。我觉得这些建筑实在太美了。具体的相片见开头的相册链接,里面附有教堂的名字和地点。要数我最喜欢的教堂就是St. Bernhard,典型的哥特式风格。另一个典型哥特式教堂是Christuskirche,我也很喜欢。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Lutherkirche,从外观上看有点像罗马风格建筑,但它却是以马丁·路德为纪念主题的,墙壁上有他的雕像。于是准确的说这个教堂应该是仿罗马风格。不过我也不是建筑学专家了。
我之所以这么喜欢这些中世纪建筑是因为我喜欢打帝国时代游戏。帝国时代游戏里对每个民族的文字介绍和音效都非常棒。Karlsruhe地处“黑森林”地带,而帝国时代就有个地图叫黑森林。当然尽管Karlsruhe城已经“升级”到差点拥有核武器的级别了,但是很多建筑却不是像游戏中那样全部换风格,而是保留古老时代的风格。相比之上北京就真的跟帝国时代里的“升级”一样,一升到新的时候,老的建筑风格就变成了新的建筑风格(拆了重建)。
Karlsruhe的人物
Karlsruhe有很多路名是名人的名字。其中在KIT校园里有一条Fritz Haber Weg,在城南有一条Kant strasse。除了路名之外,还有很多纪念人像。例如Carl Benz和Heinrich Hertz。这些人也不用我再介绍了。此外,还有Franz Grashof的像,在传热领域有一个以他命名的无量纲数:格拉晓夫数。更早一点的是自行车发明人Karl Drais。
Karlsruhe的花花草草
 |
| 05-15-2011 Flowers in Karlsruhe |
也许并非Karlsruhe城的专利的是,整个城市的阳台都有种花。人家楼房的没有防盗网,也没有分体式空调的压缩机。我去的季节正好是春天,所有花都开。最多的是玫瑰。广州之所以叫花城,原因只是说这里一年四季都有花,尤其是在本应天寒地冻的农历新年搞花市,但却不是指广州市到处都种花。恰恰相反,不去年夜花市或者专门的花卉市场的话,很难看到密集的花朵。
飞机上的感受
 |
| 05/15/2011 on airplane |
这是我第一次搭过夜的飞机,所以我能够看到日出和日落以及中间的漫长黑夜。返程飞机从德国经过整个东欧和中亚,从新疆进入中国,穿过塔里木盆地之后,南下至目的地香港。
日落自然美丽,但到最后眼看最后的余光在西边消逝,取而带之的就是从东漫延过来的黑暗,也第一次感到黑夜给人类的恐怖,也特别切身地体会到火的发明给人远古人类以多大的慰藉,难怪要歌颂。在黑夜中向下望去,虽然没有云层遮挡也几乎看不到亮光,从地图上看到,已经在中国的西境,那里是人烟稀少的沙漠和高原。我心想,要是这一掉下去死不了,岂不成了野外求生?我连火都不懂生。当然,也有经过一些城市的时候,这时就能看沿着道路散布的亮点形成的城市轮廓。也许住在城市里的人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从高处俯瞰被自然的荒蛮所包围的城市文明,总感觉这一小块“低熵”区域的维持十分不容易。很难想象我们为什么敢如些放肆地破坏本来处于这种微妙的“稳态”的环境。更多的时候往下看到的只是零星的孤独的灯光,也许是来自山区里的人家。地与天都被黑暗统治着,就会强烈的感觉下面的灯光跟上面的星光是一回事,只有中间飘着点微微泛白的云,心情突然又从畏惧马上变得浪漫,觉得自己真的是飞入了童话里描述的那种夜空,心里默默地配乐“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
差不多到广州的时候,我在飞机上目睹了日出的全过程。虽然也很美丽,心情也很兴奋,但却不如黑夜那样让我思绪万千。难怪“震撼心灵”的那两样东西,“头顶上”的那个不是“白天”或者“太阳”之类——轮不上——而是“星空”。另一个是“心中的”。人类的心灵应该既受自然的震憾也受自己的思想的震撼。而且那是要通过“反复思索”,“愈是时常愈加反复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敬畏是“有增无减”的。但我感到现在的中国人似乎离这样的文明还很远——无论是仰望星空还是道德法则,都没有进行“反复地思索”,其结果则是“有减无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