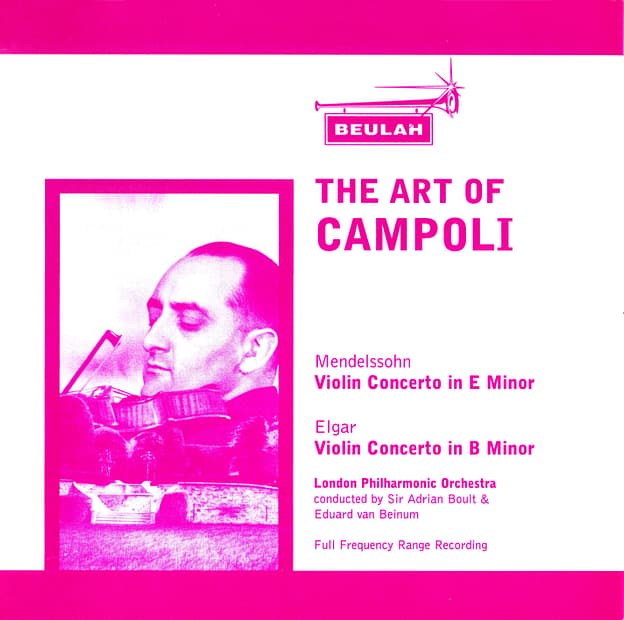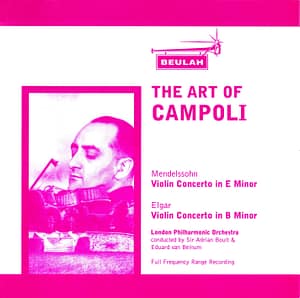网上很容易搜得到什么“六年级下册语文第二单元作文民风民俗400字”之类的关于各地饮食习惯的资料。到底以面食为主还是大米为主估计主要是决定于当地哪种东西比较好种,因为古时候粮食运输不像今天这么自由。我是广州城里人,在我印象中天天吃白米饭在旧时是不常见。广东农村应该主要是把米煮成粥,里面加番薯一起煮叫“番薯粥”,就点萝卜干作为三餐的主食。只有县城大户人家才天天煮白米饭,仆人先要把主人一家老老小小的饭和菜全部做好,盛在玲珑瓷饭碗中。工人和主人要分开吃,工人吃的跟主人当然也不一样。网上搜到一篇文章说“广东人”,其实里面的很多事情是专指广州老城市民:
人所共知,广东人日食三餐都以大米为主食。所谓“北人嗜面、南人嗜饭也”。此种饮食风俗习惯,是由广东农业耕种以水稻为主这一客观条件决定的。
广东地处南疆边陲,属于亚热带气温区。气候温暖湿润,水源充足,“民以水田为业(宋王象《舆地纪胜》)”,稻饭羹鱼。所以,粤人自古“以粘为饭,以糯为酒(《南越笔记》)”,及至现在,大体仍是如此。
现在广东一些城市生活节奏加快,面食制品增多,面食日趋兴起,甚至有食西餐、快餐的。但就日常生活而言,仍以大米为主食,有所谓“未见米落肚,不知饿定饱”,或饭,或粥,或米制的糕点,保持此种传统的饮食习惯。
广东有云许多口头禅和土语,其组词表意都与“米”字有关,如说人死了,谓之“不食广东米”;说家中增添了一口新人,谓之“加多了一碗饭”,这与来客人“加多一双筷”有不同含义;再有骂人好食懒做,广东人会说“蛀米大虫”,当然,它与我们的标题亦是两种含义;若批评人办事无能,谓之“食贵米”;批评人做事不知危险,谓之“嫌米贵——不知死活”;若挖苦人不开窍,谓之“食馊米”等如此类的说法,都万变不离其宗,说来的确离不开“大米”。把“大米”与生老病死、勤劳懒惰、精明愚蠢联系在了一起。大米在广东人生活中之地位何等重要,由此可窥一斑了。真正的“蛀”米大虫属也!
我人小则属于“食失米”,吃饭不长个儿。现在我自己就天天煮饭。自从住回补校,我自己做饭之后,我就很少在外面解决。因为任何饭馆的美食都很难比得上我自己在家弄的住家饭。先不谈外面餐馆用的油和食材很可能有猫腻,在家里做饭有一个独家的体验,就是饭在煮的过程中你能闻到饭香。因此,在家吃饭一定先闻上十几分钟的饭香才能开吃。以前跟父母住的时候,无论我在电脑前有多么不愿意停止,只要开始闻饭香,不用我妈催促,我自动就愿意放下手中的工作了。下馆子和叫外卖虽然都比自己煮方便,但是在外加班的打工族却往往吃无定时,原因就是他们直到吃饭之前都闻不到饭香。
今天在The China Beat博客上看到一本新书叫Gourmets in the Land of Famine,讲述了从1937年开始到41年最高峰的广东饥荒的来龙去脉。虽然按照Emily Hill的书评所述这本书有史料不足结论过于大胆之处,但是其将广东人对大米的挑剔作为饥荒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观点至少很有趣,恰好应验了“不食广东米”这句歇后语。莫非除了“嫌米贵”之外,“嫌米贱”也同样不知死活?——就好像“嫌钱腥”一样。书中也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农业问题上过于书生气(technocracy)而进行了批评,于是也可牵强地谓之“食贵米”了。
在袁隆平研究高产水稻之前,以大米为主食的地区平民百姓基本上是大小饥荒连年不断的,饿肚子是常态。这在今天的我来看是不可想象的。饥荒也容易导致人心叵测,中国人心中典型的“省”和“防”的心态多缘于此吧。中国的平民百姓就是指农民,中国是农业大国,以前很少城市穷人的,一直以来中国的统治问题就是如何统治农民的问题。今天发生的所谓“改变执政思路”,是史无前例的事,因为“现代中国人”是一个新出现的、以前谁也没见过的、而又人口巨大的群体。他们不种地了(都打工了),也不饿肚子了(主要愁没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