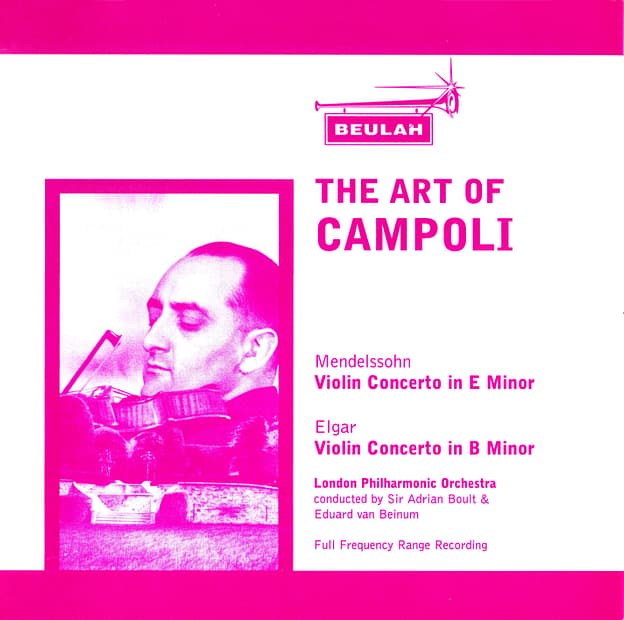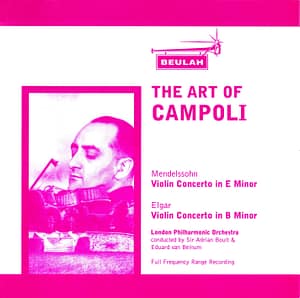前几天在SCUT Music群里的那些人还聊到英国没啥音乐家和演奏家。我也同意。Elgar的作品没办法跟Tchaikovsky相比。但是古典音乐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欣赏品位锁定在Tchaikowsky以上水平的话可选择的曲目就会变得非常少了。也许你会说一个柴D我有众多violinists的版本,但同样道理如果你把欣赏品位锁定在Milstein以上的话你可选择的版本也会变得非常少,沦为那种言必称Heifetz的菜鸟。所以就算Elgar的小协实在啰嗦,但也还不至于烂到像舒曼的小协那样变态。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舒曼小协的时候其实并不在意我听什么,原本只是随意播着一堆古典音乐MP3,结果中途突然感到非常生气,以至要放下手同的工作点开foobar确认现在播的到底是哪个作品——原来是舒曼小协的第一乐章。据传舒曼献给约阿希姆,结果后者只演了一次就把谱子扔了。舒曼自杀了之后约阿希姆还进一步猜测这个作品是舒曼发神精病的产出。
当然,现在我都经过了梅西安的历练之后,对舒曼小协就接受很多了。至少它的音乐语言是经典浪漫主义的风格,每两小节每两小节地听至少都是悦耳的动机,只是小节数多了之后就不太了解它到底要干嘛。再说约阿西姆本人就很愤.
回到Elgar,所以他作点曲子还算“为丰富古典音乐曲目”做了贡献。也可能是英法历来不和的缘故,英国稍微出点够格的音乐家就会被珍惜成为国宝,又封爵又什么的。作曲家Elgar和钢琴家Curzon都是爵士。那时候爱国主义在欧洲还是属于很高尚的。又要扯回到舒曼小协。虽然经过约阿希姆和舒曼遗孀唱衰之后这个作品基本上是萎了,但1937年有人把谱子寄给梅纽因之后他评价不低因此要为这个作品搞世界首演。可是这个谱子的版权还在德国,而德国政府坚持这个作品的首演必须由德国演奏家在德国本土进行。这种要求就跟现在我们这些中国人一直坚持敦煌文化的研究一定要由中国人在中国本土进行,为日本研究者的优秀研究而感到遗憾的古怪情绪差不多。结果虽然梅纽因后来也录了舒曼小协,这个作品一开始是Kulenkampff首演和录制的。
Campoli是英国籍的小提琴家,本人是意大利裔的。所以严格来说还不算是“英国出品”。在英国拉小提琴想出名,当然要靠拉英国国宝级作曲家Elgar的作品啦。所以你去查Campoli的介绍,就会说他的代表性录音是Elgar小协。你查Sammons也一样,还被称为“咱英国的Kreisler”,酸得很。否则干嘛非强调我能把Elgar小协拉得特好呢?别的比如门小协能拉到“较好”水平也比“能把Elgar小协拉特好”更吸引啊。事实上Campoli就是门小协拉得很好。1950年1月的《留声机》有一段评价挺有意思:
I applaud Campoli’s courage and independence that, at a time when most of the race of fiddlers seem determined to turn the Mendelssohn concerto into a vehicle for display, he should think of this work as music and not in terms of vulgarised glamour. His performance is indeed thoughtful—even including the cadenza—and the relief of listening to someone for whom the music comes first after some of the hustlers we have heard recently comes as sweet balm in the existence of a harassed critic.
最爱看这种文雅地含沙射影文章了。尤其是那个“vulgarised glamour”,真是把那种目光斜视心生冷笑之情表露无遗啊无遗。事实上比Campoli勇敢但仍负有名声的人多了去了。例如Kremer就是一个怪胎。从Campoli录的三个常规小协(门、柴、贝)来看,此人绝对上乘,非常安全。事实上Curzon虽然是安全度极高的钢琴家但是他的柴一有好多地方还是小piss off了我一下,不应该啊不应该。
原来算算时间,Campoli的门小协录音出来之后没多久,著名的Heifeitz/Beecham版也出来了。活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上流真是幸福!希特勒真是万恶,全赖他这么个好的欧洲就毁了。但是悚人听闻的是,Campoli版比Heifeitz版在当时更受人欢迎。Design Review上有段评论就是这么说的:
At the time of writing it is not known whether the (Campoli) Mendelssohn concerto will be released in this country. There is another new version from HMV, featuring Heifetz and Beecham, which it is expected, will be offered here.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general consensus of opinion overseas is heavily in favour of the Campoli performance. The work is flawlessly played by the soloist, well accompanied under van Beinum, and recorded as well as Decca know how. A pleasant point is that the first movement ends in the middle of a side — thus the effective link which the composer supplied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movements is not lost by having to turn over the disc. It is many years since we had a release of this most pleasant of violin concertos — of the three older sets still surviving in the catalogue my choice would be for the Szigeti-Beecham. I rather think most prospective buyers will await the Campolil!
由这段评论来看,在当时Campoli版和Heifeitz版都尚未在英国上市,但在海外已经各有口碑了。而且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留声机年代唱片要换面对三乐章的协奏曲们是多么尴尬的一件事情——尤其是浪漫主义作曲家们全都喜欢把三个乐章连起来。Szigeti/Beecham也是我虽本无须但俨然极力珍藏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