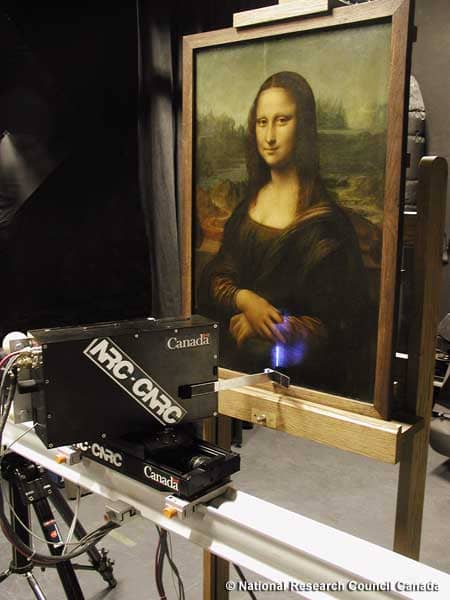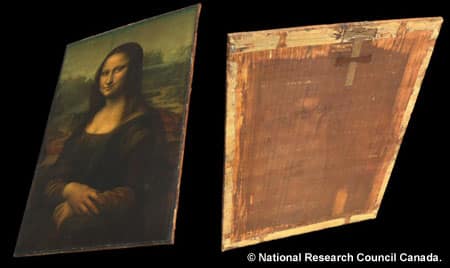《新知客》约稿,勿转!
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三位与钯催化反应相关的三位化学家:铃木章(Akira Suzuki)、根岸英一(Ei-ichi Negishi)和理查·赫克(Richard F. Heck)。
有机合成有多难?
提起化学也许有些人会想到新华字典后面的元素周期表,有些人会想到中学课堂上的球棍模型。化学研究就好像玩积木,从五颜六色的元素周期表里挑出合适的球,然后棍子搭出各种各样的分子来。球和棍毕竟只是模型,真正的化学反应往往是打碎一个现成的分子,然后变换结合出新的分子,需要在试管和烧杯中实现。分子是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一滴水中的水分子数量,要在1后面加23个0。所以化学实验针对的总是极其大量的分子。指挥两三个人同时向右转也许都不用训练,但是指挥一个营的人同时向右转就非常困难。就算再训练有素的队伍,人多起来总有个谁先谁后,不可能严格同时。化学反应也是这样,一万个分子中,谁能保证没有一两个例外的?何况是1加上23个0这么多个分子,肯定有的转得快,有的转得慢,有的还转错方向。糟糕的是,你要是不喊停,转的快的就继续转,转过头了;你要是喊停,又会好多转的慢的没转到位。因此,凡是化学反应,总会或多或少伴随有副产物。
无机物分子就好像训练有素的队伍,绝大多数无机化学反应的产率都是超过90%的;但是有机物——即以碳基化合物——就好像一群不听话的孩子。碳-碳键的形成尤其困难,而一旦形成又比较稳定。做一个有机化学反应,就好像你明明叫向左转,最终正确转了的只有三四十(产率低)。对于大多数有机合成任务,需要进行的化学反应还不止一步。等你喊上十几个口令之后,一百个分子也许只有一两个顺利到位了,而且它们还混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错误分子中,得你去把它们纠出来(分离困难)。因此,尽管在纸上可以随便画几个碳原子,用短横线连一下,就能设计出一个有机物来;但是在烧杯中指挥上亿个分子实现这样的物质来就很头痛。
现在,在一个最普通的现代人触手可及的生活周围,全都是有机合成功业的产物。家里所有的塑料和橡胶制品,许多抗生素和镇痛类药物、洗涤化妆用品甚至于部分食品,都是人工合成的有机物。所有这些组成我们现代生活的物质的发明和生产均需要高效、准确地碳-碳键。拜钯催化反应所赐,除草剂氟磺隆(Prosulfuron)、镇痛药萘普生(Naproxen)、平喘药顺而宁(Singulair)等药物年产量已超过1吨,极难分离的抗肿瘤药物Discodermolide的人工合成研究,也有钯催化偶合的功劳(图)。
因此,往往纸上那一条连接两个碳符号的小横线,一旦实现了就会引起产业的革命。在诺贝尔化学奖的历史上,已经有多次奖项颁给了关于形成碳-碳键的研究者。其中,所有有机合成实验员的最爱——格氏试剂——的发现者,法国化学家格林尼亚(V. Grignard),就获得了1912年的诺贝尔奖;而195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则颁给了发明Diels-Alder反应的两位化学家(O. Diels和K. Alder),该反应被誉为化学反应中的蒙娜丽莎;196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Ziegler-Natta催化剂的发明者K. Ziegler和G. Natta的工作,使得聚丙烯材料得以商品化(例如现在市场紧俏的乐扣牌塑料制品)。他们的工作,画在纸上,都无非是碳-碳键的形成。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也不例外——它在现代工业中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上述工作的意义。以获奖者命名的三个反应:Heck反应、Negishi(根岸)反应和Suzuki(铃木)反应几乎触及到了当今化学包括新药合成、新材料、有机光电显示等的所有研究领域,与普罗大众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息息相关。
获得诺贝尔奖的碳-碳成键反应,瞧瞧横线画在哪儿:
纪念沟吕木勉(Tsutomu Mizorok)
格氏试剂、Diels-Alder反应、Ziegler-Natta催化剂、Heck反应、Suzuki反应……所有这些有机合成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名字也同时成为了他们发现的化学反应的名字。一本厚厚的“人名反应”手册是所有有机化学研究生必备的参考书,现在甚至还有人名反应速查的iPhone软件。用人名来命名反应是有机合成研究圈子的一个独特现象。没人考究过这一传统是如何形成的,但是可以想象,麻烦的反应,很快会被后人忘却;而那些非常受欢迎的反应,则一定会被经常提起。用一个名字来代替,总比每次都从反应物到产物描述一遍来得简单多了。至于使用反应的发现者来命名,也是出于尊重前人劳动。久而久之,人名反应实际上就变成了有机合成化学家的实用“工具箱”,留下来的全是精华。
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一R. Heck的名字也被用于他发现的反应了。除了叫“Heck反应”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用“Mizoroki-Heck反应”。这个Mizoroki是一位日本人的名字(Tsutomu Mizoroki,沟吕木勉)。
R. Heck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在美国Hercules公司进行研究工作。他长期对少人问津的过渡态金属(就是元素周期表中间黄色的那那堆元素)十分感兴趣。1968年,Heck在美国化学学会会刊发表了一篇关于通过钯催化剂的辅助形成碳-碳键的论文(J. Am. Chem. Soc. 1968, 90, 5518–5526),但是在这篇论文里的例子中,使用到了含汞和锡的化合物(有毒),而且需要较大量的钯(昂贵),因此虽然该反应十分干净利落但还是不尽人意。
时隔两年,大洋彼岸的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副教授沟吕木勉在日本化学会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Bull. Chem. Soc. Jpn. 1971, 44, 581),既避免了汞化合物的使用,又大大降低了钯的用量,成为了Heck反应的第一个完美的范例,也是直到今天一直被使用的版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Heck反应的成功是沟吕木勉实现的,称为Mizoroki-Heck反应当之无愧。尽管R. Heck在此后发表的文章中都诚实地引用了沟吕木勉的工作,然而在当时,还是Heck的名字明显更加响量。直到90年代,日本化学家辻次郎在编写一本关于钯催化反应的专著时,采用了“Mizoroki-Heck反应”的说法。辻次郎解释说,在六七十年代,《日本化学会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期刊,尽管Heck在此后发表的论文中都注意引用了沟吕木勉的工作,但在西方化学界,看过Heck论文的人还是远比看过沟吕木勉论文的要多得多。
而沟吕木勉却在论文发表的9年之后,过早地死于胰腺癌。
R. Heck此后的人生也并不美满。尽管自八十年代起以Mizoroki-Heck反应为灵感的钯催化交叉偶合反应研究广泛地成为热门,但Heck本人却由于无法申请到科研经费,于1989年提早退出了科研圈。幸运的是,他一直活到了今年,尽管几乎整个化学界都认为给Heck的诺贝尔奖化学奖颁得太迟。
Heck这样描述已故同行沟吕木勉的工作:
称为Heck反应还是Mizoroki-Heck反应其实都没所谓。确实,沟吕木先生首次发现了这一反应,但是我也没落后太多,并继续进行钯催化反应的研究。而他似乎并没有马上认识到这一反应的价值。可惜他去世得太早了,否则今天这个反应可能就会被直接称为Mizoroki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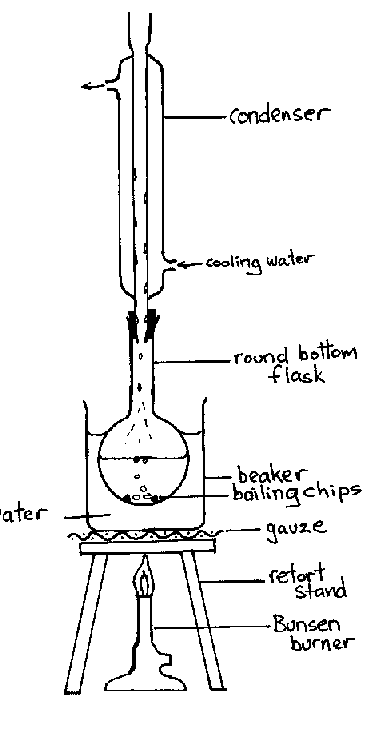

.png)